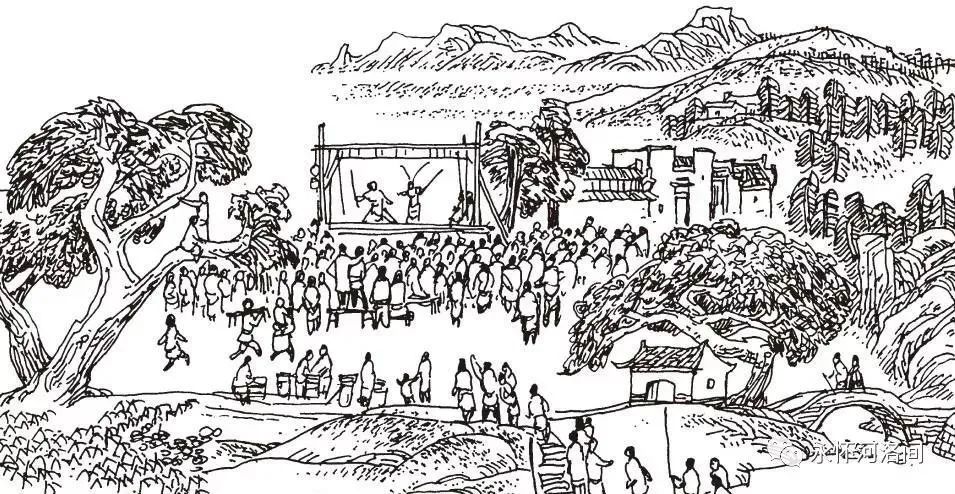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尾,我出生于山东潍坊北部的农家。
那时的乡间生活,尽管麦子面粉这样的细粮,仍旧一如既往的稀罕,但是地瓜、玉米棒子等粗粮,几乎连年丰收,已然极少听说有吃不饱肚子的事件发生。
至今想来,生产队时期,几乎年复一年,每到麦收时节,田坡里收回来的麦捆,解捆暴晒之前,在生产队的场院内堆放,重重叠叠,犹如连绵起伏的金黄色丘陵。
农谚有道“三秋不如一麦忙”。盖因麦收季节,强对流天气频发,电闪雷鸣伴随着瓢泼大雨,往往突如其来。
柴油机传动脱粒机,日夜震耳欲聋的,歇人不歇机。大约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,方能够脱粒完毕。
昼夜劳作,连轴运转,本来疲惫不堪的人们,对于夜班,竟然趋之若鹜。
原因在于,夜班的人们,除“工分”翻倍之外,尚有一项平日里难得的福利,便是每到午夜时分,交接班的社员,可以在场院高杆上悬挂着的几盏雪亮汽灯之下,享用一顿油光可鉴的西葫芦菜汤,外加几大笸箩可以管够、管饱的麦子面“细单饼”。

这种入口绵软且劲道的“细单饼”,一张或者几张,卷起来“拤”在手上,呈紧实的筒状。早年间,日子宽裕的财主人家,除了可以卷入大葱、咸菜,甚至土豆丝、炒鸡蛋、猪头肉之类相当奢侈的“硬”菜,在麦收这类繁重的农活儿期间,管待干活儿的长工或者短工。
这就是莫言先生所著述《红高粱》当中,多次描述过的——那种使得一众“山东高密东北乡”土匪为之心驰神往、不惜冒着杀头风险,上山入伙儿的“拤饼”。
作为“闯关东”人群的主要发源地,取直改道之前的潍河流域,古来多灾多难。
我至今难忘流传于早年家乡的一首俚曲:张刘二车道(村),辛庄(村)玉皇庙(村),不是雹子打,就是河水涝。才得(刚要)还还阳,“胡子”来绑票······
不止是莫言先生老家的“高密东北乡”,其实在我毗邻渤海莱州湾的老家,也不止一桩听闻过类似的陈年旧事——沿海偏僻的农家,经常不幸被海上的“胡子(海盗)”或者兵匪难辨的“杂牌队伍”绑了票去。
实在凑不够赎金,那就杀一头猪,再挨门挨户跪求全村的“娘们儿”一起支起鏊子,烙上几笸箩“细单饼”,托“中人”送到指定地点,十有八九,竟然也能将人“全须全尾”的赎回。
建国之后,“胡子”们终于绝迹,潍河也再没有决堤。
挺过期间的三年“自然灾害”,之后的一段岁月,尽管各种“运动”接踵而来,庄稼仍旧年复一年的耕种。

一日三餐,镇日少不得玉米棒子面窝头咸菜。更有“贫寒”之家,常年水“发(浸泡软化之意)”了地瓜干子,到得举炊时,主妇们上锅隔水蒸熟,便是全家的一日三餐。“吃饱穿暖”情结之下,大人们无不传承一个知足。
只是每到“揭锅”开饭时分,往往有不懂事的孩子,面对那一垫子令人泛酸反胃的熟地瓜干,恐惧到声泪俱下、嚎啕大哭。结局大多是少不得挨上家中爷们儿结结实实几个鞋底,外加一顿暴跳如雷:“狗日的东西,难不成真得像你爹娘早年一样,要拖着打狗棍子‘出庄跋疃’,尝几年要饭的滋味儿咋的?”
所谓“出庄跋疃”要饭,确实是早些年遭遇“年馑”的常态。
我的几位姨、舅等近亲长辈,后来非止一次描述,他们曾于某些年的冬春季节,领着兄弟或者姊妹,到“围城靠店”的相对富庶之处,出门讨饭的经历。
之所以忍心派几个孩子“出庄跋疃”,盖因当时“政策”,成年人是为“在册”之劳力。贸然外出讨饭,一旦被值守或巡逻的民兵截获,“劝返”事小,吓人之处在于,会被冠一顶“恶意讨饭”的帽子,遭遇批斗或者游街,不免丢人现眼。
春季讨饭,缘于青黄不接,多会当天往返。而冬闲时节要饭,盖因天寒地冻,讨来的零星面食便于晾干保存。装满一条布袋,便会轮流扛回家中,随后重新上路。
大雪动辄铺天盖地的要饭途中,夜间歇宿的地方,多是所到之处,各村的好心之人铺垫了麦秸,却难以抵挡四壁透风的碾屋。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,使得当下生活已然富足,然而人生已然垂暮的他们,至今感情格外亲近。
即便风调雨顺,奢望几顿细粮,须得熬到过年。
一进腊月门儿,便有满街的《忙年歌》唱道: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粥,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。二十三,糖瓜粘(祭灶之贡品)。二十四,扫房子。二十五,做豆腐。二十六,煮点肉。二十七,杀年鸡。二十八,贴窗花。二十九,蒸馒头······”
童谣历来大多是如此红火煽情,“年”也毕竟与寻常日子不同。然而真相是,肥硕的公鸡,是可以用来换钱的。而能下蛋的母鸡,倘若因为过年被杀掉吃肉,家中老婆十有八九会与“刽子手”拼了“血”命。因而,再嘴馋、再有“过年情结”的汉子,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民间另有俚语形容庄户日子“掺水”之程度,道是:“(煮)一个(肉质腥膻因而不值钱的)老母猪打上十八担水”。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,过年“煮点肉”倒可能确有其事——忙活一整年,再不济的人家,大抵都会称一小块儿肥多瘦少的猪肉,剁入自产自收的白菜、萝卜以为“肉馅”,算计着捏几顿饺子,烘托年味儿。匀出少许,每人煮一碗稀薄的肉汤,便堪称“过了个肥年”。

唯有豆腐算得亲切。听闻挑担串乡的豆腐梆子敲响了,端一瓢金贵的黄豆,兑换或大或小的一方,冻成蜂窝状,熬白菜自不必说。通行的吃法,乃是上锅蒸过,待其结为硬实的一坨。出锅凉透之后,下刀切作条块,撒上细盐,腌得齁咸,充作年节期间下饭的珍馐。
至于蒸几锅馒头,年初三之前贡献天地、祖先之外,尚需“锱铢必较”,当做正月里携带上门“攀亲”的节礼。故而除却乡村里在职的大队、生产队几层“官宦人家”,如若另有人家连贯食用到初三“圆年”之后,便真的堪称举村罕见的“殷实”人家了。
时至今日,即便不是过年,馒头和“拤饼”这种往日罕见的面食,也早已成为家乡寻常百姓的日常主食。
如果不再有天灾人祸,曾经的要饭,特别是一度受过民兵管制的“恶意讨饭”,大概会成为永远的过往。
除了吃饭穿衣这一桩,自古及今,农人们根深蒂固的觉得,鞭炮齐鸣“过大年”的那几天,毕竟不同于寻常的日子。
只是,壬寅虎年,家乡人的“大年”,不见了数千年来鞭炮齐鸣的那种普天同庆和喜气洋洋。
据坊间父老传闻,原因在于,“上面”有人要求,过大年期间,包括了农村的“全域”之内,凡“擅自燃放烟花爆竹”者,皆属于“恶意过年”。
“情节严重”的,一旦被逮住,“罚款”之外,是需要到“号子”里面去蹲几天的。